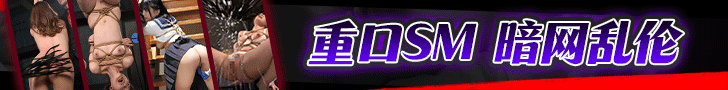交合处白沫四溅,喷在青黑的树皮上,淫靡又色情。
谢稚白听见怀鱼的话,眼底染红,放肆地抽插起来。
啪啪。
……
怀鱼被肏得呼吸都不能了,窒息的感觉涌过头皮,指甲用力到发白。
短促而深入骨髓的高潮让他的狐狸眼上翻着,像是被玩坏了,他抱着树干企图减轻被谢稚白肏干的震颤感,却还是被插得肚皮隆起,肉芽失禁。
稠白的浓精射在他的后庭里,烫得媚肉四散奔逃,没过他的肠道。
他真要死了。
在谢稚白松开他腰间的手那刻,怀鱼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让谢稚白进屋,但又实在累得开不了口。
他的衣裳早已被谢稚白脱了个干净,谢稚白自己的衣裳却还穿着,天水碧常服上全是他的白浊,下摆都湿透了。
“进屋……唔,会……会被发现。”
怀鱼还记着侍女去看热闹的事,稍稍恢复点力气就催谢稚白回屋内。
谢稚白:“不着急。”
他不着急,怀鱼不能不着急,要是让侍女看见,就是看他的热闹了。
怀鱼急得直哭,央求着谢稚白抱他进去。
谢稚白又说了句还早,抱着少年到花圃间,让他跪在草地上。
他变幻出两个分身来,一个跪在少年的身前,揉着少年的乳果,龟头蹭着少年的嘴角,马眼处的白浊怼弄进怀鱼的嘴里,另一个舔着他的女蒂。
怀鱼惊得哭喘不止,就在他张开嘴的瞬间,青年硕大的性器就插进了他的嘴里,堵得他说不出话,哭声全呜咽在唇齿间。
肉棒又大又硬,像石头卡在他的嘴里,少年的嘴角都被撑疼了,口涎不停地流到下颌。
身下的谢稚白躺在他的跨下,清隽出尘的脸几乎要埋到他的小逼里,牙尖轻咬含吮着他的小肉蒂。
跪在他身后的青年依旧没拔出他的肉棒,欲根搅和着他射出的浓精,几乎要将他烫化了。
“唔呜……”
怀鱼的声音上扬了好几个度,夹击的刺激席卷了全身,成倍的触感让他大脑迟钝。
谢稚白舒爽得飘飘欲仙,每个分身的感知都被他接收。
少年的下颌不断地颤缩,紧夹着他肉棒,肉缝间蜜水甘甜,散发着诱人的味道,让人想插进去。
怀鱼被几个他簇拥在中间,像是被端上桌的烤羊羔,香气四溢,鲜美可口,撩拨着他的味蕾。
他也不再克制,当即开动。
少年哭得惨极了,想躲都没地方躲,咸腥的白浊推开了草芽的清新,熏得他脑袋发昏。
性器插进了他的喉管,在他嘴里进进出出。
他要坏了呜。
身下的青年也按捺不住,抽出他体内的木阳具,狠狠破开黏湿的肉壁,肏进他的宫口。
两只性器互磨着敏感的肉壁,像是被无数电流击中。
怀鱼泄无可泄,肉芽淌出稀薄的精水。
夜幕一点点暗下去,院外传来了侍女的说话声。
怀鱼警觉地呜呜叫
起来,可谢稚白依旧不为所动,对着他的小洞狂插猛捣。
洞内的媚肉急剧颤缩着,吞吐着青年的性器。
要完了呜。
他鸵鸟一般闭上眼,等着侍女惊呼出声。
心跳得快蹦出胸口,额头上冷汗直冒,臭十三,坏蛋十三!
谁知那侍女却像是没看见他一般贴着他过去了。
咦?
好像看不见自己。
怀鱼嚎哭不止,谢稚白就会吓他,欺负他,大坏蛋!
气松下来后,他又被谢稚白肏到了失禁。
谢稚白贴在少年的耳边说道,“不怕,不会让人看见怀鱼。”
怀鱼哭得惨兮兮,谢稚白是大骗子。
少年跪在花圃间,膝盖都跪红了,粉润的唇瓣被谢稚白插成了石榴红,下颌被肏得合不拢,被迫吐出口涎。
狐狸眼被插得眼波流转,眼尾更是因持续不断的高潮绯红一片。
媚色动人。
谢稚白强忍着射意,终究还是没扛住少年的含缩,齐齐交待在少年的身体里。
暖融的精液灌到少年的胃里,在发现少年承受不住后拔出了喉管,却还是有许多溅在了少年的眉眼处。
怀鱼的全身各处都沾满了精斑,包了一层又一层,无助地趴着。
他克制不住干呕起来,撅起屁股跪在花圃间哭得湿淋淋的。
“呜……”
怀鱼还没歇上一会,青年又插进了他。
小鹂站在卧房门口,见窗户大开着,朝里唤道,“尊上?”
没得到回应。
小鹂又叫了两声,见还是没得到回答,便推门进了屋,察看一圈退了出来,焦急地对侍女说道,“尊上不见了,快去找!”
怀鱼不敢和小鹂说他在这,太难为情了。
“呜,回卧房……”
谢稚白:“我同小鹂说。”
怀鱼啜泣着摇头,“不要!”
他要和小鹂怎么说啊!
四周的人都在叫他,羞耻和愧疚让他紧张地缩着前后的小穴,蠕动的媚肉没能吸到谢稚白的精液,反倒是增加了少年高潮的频率。怀鱼还没来得及消化高潮后的敏感,就又被肏到了另一波高潮,到最后少年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来了。
谢稚白收回分身,抱着少年回了屋内。
他关上圆窗,对小鹂说让她不用找了,自己堵着满是浓精的洞口,将沾满自己气息的怀鱼抱在怀里,他有点不想给怀鱼洗浴了。
少年全身吻痕斑驳,精斑错落,显然是被肏得不行,贪吃的小穴还在吞吐着他的性器,舍不得他离开。
谢稚白摸着少年隆起的小腹,还是给少年擦洗干净,抱他上了床。
次日午后,主院枫树下。
怀鱼坐在谢稚白怀里听侍女说着昨日的热闹。
高个侍女说道,“听说虞宿虞二公子现在还在偏院里呢。”
怀鱼讶然,“他这么厉害吗?”
谢稚白见不得怀鱼夸别的男人厉害,贴到少年耳边,“……才一天一夜。”
他难道不比虞宿厉害?
侍女们顿时笑作一团,“哪里是虞二公子厉害?分明是……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