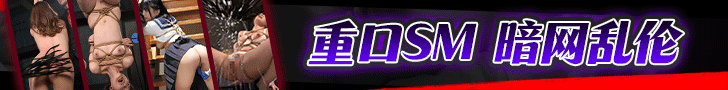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比如,嘿我想想。”安德烈略微思考了一瞬,“哦对,比如我是直男,那你完全就可以让我去操逼赚钱,他是同性恋,就接男客。我们给你表演不一样的东西,做不一样的事情。”
“…………”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把这个扩大就可以,对吧。”
安德烈信誓旦旦:“你要是觉得他纯情一点,他就当你正牌男友,围着你转就好了。我可以做到基佬做不到的事情,没准我能去外面弄个孩子给你玩玩,诶你喜欢带小孩吗?”
“小孩!?”刘一漠一整个大震惊,“不可以搞大别人的肚子!”
安德烈一愣:“啊?你不喜欢吗?”
然后他细细思考一下,又露出个坏笑,“还是吃醋了?”
“也、也有吃醋。”刘一漠坦诚地应了下来,“但不能把别人当生育工具吧喂!”
这下换安德烈郁闷了:“啊?万一有人想生呢,而且我怎么觉得当生育工具还挺爽的,这是我人生目标之一诶……”
“…………”
刘一漠心情复杂地看了安德烈一眼,然后在看到安德烈紧绷结实的腹肌时突然想到了什么,支吾几下,小声地说:“那假如,假如哦。如果你能像女人一样,被男人内射了就会怀孕的话,安德烈想被操怀孕吗?”
安德烈先是本能地回答:“想啊,给你生啊。”
然后他又细细思考了一遍刘一漠的问题,似乎是意识到什么,大脑放空了几分钟,然后回过神来沉默不语。
如果男人也能怀孕。
作为雄性被内射,然后怀孕。
那么,安德烈会……
看他许久没有说话,在安德烈臂弯里的刘一漠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安德烈?”
“你可以把我牵出去给人操。”安德烈眼睛一眨不眨地说,像是走神又像是十分集中,“操怀孕了,你让我生我就生。”
说完,安德烈抖了一下,腿稍微合拢了一些,刘一漠这才发现安德烈竟然正在喷精!
那射精与安德烈以前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最开始,在认识刘一漠之前安德烈最爱用袜子、内裤抵着龟头疯狂摩擦,然后硬着肉棒将脆弱的衣物抵死在墙或床板上磨蹭,像是在模拟抵住炮友的子宫口一般,最后射得一塌糊涂,巨量的精液甚至会在爆发时喷到安德烈的胸肌上,挂在褐色的健壮胸口。
后来随着安德烈意识到刘一漠不希望自己射精,就再也没有打过飞机,射精一般都以梦遗的形式:他会梦到巨乳长腿的女人,有时候也会梦到刘一漠光溜溜的双足,在梦里安德烈会跪下去全裸着用肉棒侍奉对方,直到他被磨喷或者对方被坚硬的巨物磨得受不了,然后安德烈会喷一些出来——哪怕是梦遗时,安德烈的射精也是汹涌澎湃的,夏天时他不盖被子睡觉,精液能喷到超过头顶,安德烈时常一觉醒来发现胸腹与脸上都是自己的精液,伴随着前列腺与些许尿液的味道,让他像是一头刚刚交媾完的肌肉野兽。
但是这次,他的喷精竟然是安静而缓慢的,就像一条些微失控的河流,或者关不上的水龙头。
那根昂扬的肉棒一突一突地,潺潺的透明淫水止不住地从里面不停冒出来,很快就打湿了他光滑的下体,顺着大腿往下流,偶尔夹杂着一股浓白的精液。
与其说射精,不如说像是潮吹了。
安德烈在安静的潮喷中抱着膝盖,忍耐从未经历过的无声高潮。
他感觉很爽,却没那么爽,爽得他肉穴抽搐、不停去贪婪地吮吸巨大假阳具,又清醒地能够感受到刘一漠注视着自己的眼神、两人正在谈的话题。
安德烈就这样在清醒中反复见证着自己的下贱潮喷——只是因为幻想自己变成会被操怀孕的肌肉爷们,只是因为幻想变成刘一漠的配种畜生。
好几次安德烈差点被肉棒传来的快感带上高峰,他很想更加不要脸地求刘一漠现在就这么做:哪怕他没法怀孕,他也不介意被男人内射。
作为一个舔狗,作为一个屁眼在同学面前被操烂了还要对对方言听计从的舔狗,他的肌肉帅哥尊严已经不重要了,他是直男也不重要了。
他现在做更贱的姿势给刘一漠看,比如绷紧肌肉把腿打开些,用两根手指顶开肉臀,把他已经被操出水的肉穴露出来。
刘一漠:“安德烈。”
“在……”
“站起来,把假鸡巴拔出来。”
“?”
安德烈一个激灵,稍微清醒了些,他看到刘一漠眼神闪烁地看着自己,像是想要认真看,又像是对性没兴趣一般。
这种态度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安德烈的头上——并非扫兴,被忽视自身需求只会让舔狗亢奋,但是这样的态度让安德雷意识到自己弄错了刘一漠的需求。
“ok,呼,等我一下。”
安德烈深吸一口气,立刻把自己脑海内的许多淫乱臆想抛在脑后。
多年的舔狗思维已经让这个威武的爷们能随时为了一个要求而放弃私欲,他的价值观与自我认同已经被扭曲到了一种机制,原本属于一个肌肉种马的自私几乎没剩下多少,全部变成了为刘一漠的利益与要求而努力的惯性思考方式。
甚至哪怕在安德烈放弃自我满足的过程中,他看着因为满意而安静地等待着自己到来的刘一漠,心底反而是升起了更大的快感,他只靠这种扭曲的快感就可以激动得去操场上不停跑圈了。
“操……”
安德烈抖着腿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本想潇洒利落地马上拔出来,结果没想到光是稍微站起来一些就快被磨得腿软。
以前两人打闹,刘一漠顶多也就是用钢笔、香肠一类常见的小东西操进去,往往安德烈会因为仅剩的一点廉耻心而红着脸不主动扒开肉穴吃下去,再加上刘一漠很少提要求,所以两人认识了许久,安德烈一直没怎么被开发后穴。
但是这次安德烈可以说是彻底被操开了,安德烈靠肉体与精神的强韧硬着头皮坐了下去,也许得益于安德雷巨大的骨骼,对普通人来说尺寸恐怖的假阳具竟然没有弄伤他,反而是有些适应地深深插在安德烈体内磨了快两个小时。
安德烈原本没有什么感觉的屁眼已经被磨得红肿外翻,充血的穴肉变得敏感,给曾经以为自己一辈子就用大鸡巴操人的安德烈带来了冲击性的异样快感,在拔出的过程中被粗粝的假阳具每摩擦一下都会让安德烈有想叫出声的冲动。
过去,只有在安德烈做爱做到快要濒临喷精、最后冲刺时才会有这种直冲脑髓的快感,他热爱在紧致的穴道内不停冲刺,感受着自己硕大涨满的龟头在失控喷射时被小穴死死包裹住。
“啊啊啊,操!”
安德烈咬着牙站起来的每一秒都感觉屁眼要被操得爆汁了,他就好像长了一个比傲人巨根还要重要、还要敏感的性器官,被道具狠狠开拓之后,又在假阳具离去时经历另一番形变,由媚肉组成的甬道不停涌出淫汁,顺着安德烈的粗壮大腿流下。
心中一横,安德烈肌肉紧绷,撑着椅子猛地一下站起来。
预想之中的肌肉抽筋并没有出现,但是从未有过如此下贱的坐插经验的安德烈并不知道,是那根粗大的假阳具抵死在自己的前列腺上、压迫并且维持着肌肉与膀胱之间的关系,突然拔出之后迎接他的不仅仅是一次抽出快感、一段空虚,还有突然放松下来的肌肉与膀胱带来的——
失禁。
“————!”安德烈在即将意识到下体时已经晚了,向来在性爱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他这次丧失了自控能力,毕竟他的膀胱可不像以前的炮友一样会服从他的意志——憋到一定程度,不管你是谁,都必须面临尿崩失控的尴尬局面。
看着就在面前的刘一漠,安德烈急忙双手遮住肉棒,尿柱有力地打在安德烈青筋粗重的手上,显得格外有男性成熟魅力的大手很快被尿液沾满,安德烈表情扭曲地忍耐着最本能的排泄快感,硬朗而阳刚的五官完全变形,丑态尽出。
安德烈一边失禁一边肉穴抽搐,前后性器官同时被折磨到极度疲劳的他面临下半身彻底地失去控制,甚至屁眼噗噗地发出排出淫液与被假鸡巴操进去的白沫、空气的声音,让安德烈刹那间红透了脸。
他的失态向来是在自己控制中的:用来取悦刘一漠的,用来表忠心的,用来发泄性癖的,用来耀武扬威地表示“我很优秀,你们没法和我争一漠”。
但是这次失禁完全在意料之外,直男屁眼就像被开苞一样被彻底操了个外翻,安德烈本想像个可靠的邻家大哥哥一样赶紧抱着刘一漠哄他,结果喷尿喷得鸡巴像开了闸般,装酷不成反而出糗,一身肌肉都遮盖不住安德烈因为喷尿而颤抖的下贱。
好不容易喷完了,安德烈浑身都是自己的汗和尿,有些不好意思抬头看刘一漠。
他知道自己将会无数次在刘一漠面前丢脸,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我去洗一下。”安德烈大手一捞,脸上红成一片,准备抱着被子和衣物去收拾干净。
“过来。”
刘一漠则不给安德烈逃走的机会,他轻车熟路地挽着安德烈的手臂亲了上去。
两人的呼吸纠缠
在一起,安德烈厚实的舌头往里面一抵几乎就能将刘一漠的唇齿填满,但是他被刘一漠小巧的粉舌不停舔舐,射精与失禁之后的安德烈很快就乱了气息,胸膛起伏越发剧烈,很快就败下阵来,脑缺氧地跟着刘一漠的指挥走:把衣服放下,慢慢爬上了床,狗趴一般在刘一漠腿边。
湿濡的吻结束之后两人都是气喘吁吁。
“呼,呼,呼……”
“真行啊主人。”安德烈对刘一漠有些刮目相看了,他挑了下刘一漠的下巴,看着上面被自己的胡茬扎出来的粉红色印记颇有成就感。
“这个是,小补偿。”刘一漠心虚地说,“这个时候我本来该把你牵到地上去好好操一顿的。”
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备忘录,里面详细地记录着各种驯化方案,大多并不成体系,但是安德烈光是看一眼上面的各种玩法就感觉自己又要热血沸腾了,刚在亲吻中被刺激得硬起来的巨根甚至隐隐有涨满的架势。
那些是在刘一漠能提供和接受的范围内,安德烈喜欢的玩法,充满着两人的行事风格,就像是一份色情版的“情侣应该一起做的一百件事”清单。
“你什么时候列的这个备忘录啊?”安德烈挑眉。
“有时候想到就记一下,免得没性趣的时候又要调教你嘛。”刘一漠嘟嘴,“算是小抄吧。”
安德烈幸福得眯起眼睛,露出来一个像是被撸下巴的狗一样开心到冒泡的傻卵表情。
【啊,他还列了个性冷淡的时候当备忘录的清单,一漠心里有我。】
“诺,‘第一次把安德烈玩尿’和‘开发后穴’之后,我觉得应该是要再肏你到你受不住,这样才能记住感觉,”刘一漠心情复杂地收起手机,“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对你说,这个超——级重要,不说出来我总觉得安不下心来玩你。”
“没关系啊。”
安德烈耸耸肩,他换了个姿势跪在刘一漠旁边,伸出一只手给刘一漠抱住,既像可靠的男友、又像一只守着主人的大狗。
安德烈是个性欲极旺盛的家伙,而刘一漠则容易性冷淡、注意力从性上转移,似乎对刘一漠来说有很多比性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就经常会出现安德烈被使唤到喷精高潮,但是他还没高潮完刘一漠就失去了性质的情况,两人的性欲节奏经常对不上。
被放置是安德烈很经常遇到的事情。
“我是舔狗嘛,被放置我还挺爽的。”安德烈痞痞地笑着,在刘一漠的鼻子上舔了一下,“老子就是舔狗的极致好吧!”
刘一漠又好气又好笑地擦了一下湿漉漉的鼻头,被安德烈逗得放松了。
“想和我说啥?”安德烈轻声问。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刘一漠闭上眼睛,躺在安德烈的怀里,感觉自己被世界上最厚实的山脉给包裹着。
“讲一个,关于真实的刘一漠的故事。”